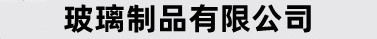万向挂机软件下载首页:百事注册:首页,万向注册=登录首页世界上最早的“原始玻璃”——费昂斯(faience)出现在公元前五千纪末到四千纪初的西亚、埃及地区,最早的成熟玻璃出现在公元前三千纪末的西亚、埃及,公元前两千纪中叶,这些地区开始了规模化的玻璃生产,西亚、埃及地区成为世界早期玻璃技术起源和制造中心。自青铜时代开始,玻璃制品及玻璃制作技术,由上述地区向周边传播,经由西亚、中亚以及我国新疆地区、河西走廊,继而进入中原地区。系统梳理新疆古代玻璃的发现与科技研究成果,厘清新疆地区古代玻璃制品分布演变的时空脉络,对于探索我国玻璃技术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
费昂斯是一类内部为烧结的石英胎体、外表施釉的玻璃质材料。在以往国内外的研究中,往往将费昂斯看作是玻璃的前身或“原始玻璃”,因而它在玻璃起源以及玻璃技术发展史的研究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世界上最早的费昂斯制品于公元前五千纪出现在埃及、西亚地区,我国费昂斯的出现较西方晚得多,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费昂斯制品出现在青铜时代中期的新疆地区,年代约在公元前1800~前1500年,这些材料对于探究我国费昂斯技术的起源问题至为关键。
过去我国费昂斯技术的研究对象多为中原地区出土的费昂斯制品,年代上至西周下至战国,器型以小件珠饰为主,成分上与西方相比,呈现出高K2O的特征(Na2O/K2O<1)。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丰富和科技考古研究的逐渐深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新疆地区出土费昂斯的研究,试图以此探寻我国古代费昂斯技术起源的新线索。目前,公开发表的新疆地区出土费昂斯相关研究成果虽不多,但该地区早期费昂斯的特征已开始被关注,对于新疆早期费昂斯技术与中原地区以及西方费昂斯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探讨日渐深入,新疆早期费昂斯技术源流初见端倪。
新疆地区出土费昂斯制品的科技考古研究,最早见于刘念等对哈密亚尔墓地出土费昂斯珠饰的分析。该研究采用了ED-XRF和SR-μCT等分析手段,对亚尔墓地出土的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公元前1050~前300年)的费昂斯珠饰进行了无损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该批费昂斯制品可能采用了直接施釉或风干施釉两种施釉工艺,均以内芯成型法成型,且多数样品Na2O/K2O>1,表明这批费昂斯珠饰可能来自西方或配方工艺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根据成分分析结果,作者提出我国西周时期的费昂斯技术可能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从西亚经新疆传入,进而为我国费昂斯技术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可惜的是,该文所采用的成分分析方法是ED-XRF表面分析,所得到的分析数据助熔剂成分含量显著偏低,这可能是受到了样品表面风化的严重影响。所以,该批费昂斯珠真正的来源,还需依赖于后续对该墓地出土更多费昂斯制品微区玻璃相成分的进一步检测。
此后,林怡娴等和王颖竹等先后发文对新疆地区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阿敦乔鲁墓地出土的费昂斯制品进行了研究,这两篇文章所涉及的材料将新疆乃至整个中国的费昂斯制品出现的时间上限提早至公元前1800年前后,为我国费昂斯技术起源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
其中,林怡娴等对哈密天山北路墓地M200出土的四件费昂斯珠饰进行了分析,其中三件为多节连珠型费昂斯珠,一件为细长管状费昂斯珠,其年代在公元前1500~前1400年,分析结果显示该墓地出土费昂斯制品中3件为混合碱型费昂斯,1件为疑似富钠型费昂斯。哈密天山北路墓地文化结构复杂,有与河西走廊马厂晚期、西城驿文化和四坝文化一致的文化因素,亦存在与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特征一致的青铜器和陶器等文化因素,以该墓地为代表的天山北路文化是在东西方文化因素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性文化,该文化相关遗存表现出明显的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的特征。林怡娴等认为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费昂斯珠饰无论从器型还是成分特征上都与北高加索及欧亚草原出土的费昂斯珠饰联系密切,很可能是从这些地区经中亚直接传入新疆,这一结论与该墓地出土的部分陶器和青铜器体现出的与北方草原之间的源流关系可以互证。但是,该文也注意到,虽然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费昂斯珠饰年代早于中原地区最早的费昂斯珠饰,由于其成分和器型特征均与中原地区主流的富钾型费昂斯差异较大,因而中原地区早期费昂斯技术的起源与新疆东部地区的费昂斯之间可能并不具有关联性。林怡娴等的论文发表后不久,杨益民对其成果进行了评论,认为前者论文中所分析的青海上孙家寨费昂斯珠饰在年代确定上存在问题,并重申了新疆哈密地区费昂斯技术对西周时期中原地区费昂斯技术的显著影响,指出新疆哈密亚尔墓地和西周倗国墓地出土的管状费昂斯珠饰运用了相同的施釉(风干施釉法)和成型工艺(内芯成型法),并认为二者在技术上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西周时期的费昂斯技术可能同块炼铁技术一道,从新疆地区经河西走廊传入中原地区。
此外,王颖竹等对阿敦乔鲁墓地出土费昂斯珠饰进行了分析研究,该批材料出土墓葬经碳十四测年年代在公元前1689~前1528年,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费昂斯制品。阿敦乔鲁墓地的费昂斯珠均为多节连珠形,从成分分析结果看,均属混合碱型费昂斯,在成分和器型上都与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费昂斯珠饰相似,研究者认为该批费昂斯珠饰可能是从欧洲传入新疆西天山地区,继而东传经天山廊道进入哈密盆地。阿敦乔鲁墓地位于西天山北麓,向北越过天山支脉便是巴尔喀什湖东南岸的七河流域,再向西、北与欧亚草原相连,阿敦乔鲁遗存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费德罗沃类型(Fedorovo)和七河类型早期关系密切。林怡娴等在七河地区青铜时代的墓葬中也发现了与阿敦乔鲁墓地类似的多节连珠型费昂斯或青铜珠饰,安德鲁·绍特兰等认为此类珠饰在东欧草原历史悠久,自洞室墓文化(公元前2600~前2350年)时期就开始流行,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存中普遍发现。据此,可以推测阿敦乔鲁墓地混合碱型多节连珠费昂斯珠的出现,可能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费德罗沃类型晚期及七河类型早期向天山地区迁徙、扩张的历史背景相关。
截至目前,虽然对新疆地区早期费昂斯的科技分析成果还不多,但该领域的研究已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特别是对新疆青铜时代中期费昂斯的研究,目前已基本明晰其源头在北高加索,可能经北方草原传入天山廊道继而进入中原地区。相较而言,目前对新疆青铜时代晚期到早期铁器时代初期费昂斯制品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而这一时期(公元前1000年前后)正是中国本土费昂斯技术起源的关键阶段,对这一时段新疆出土费昂斯制品的技术特征的深入分析,有望为进一步探讨我国费昂斯技术起源问题提供更多线索。
约在公元前两千纪末开始,新疆陆续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公元前一千纪中叶,游牧文化在新疆地区进一步深入、普及。这一时期,新疆地区的先民开始使用成熟的玻璃制品。新疆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的玻璃珠饰,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成熟玻璃制品,其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1130~前620年,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春秋时期。干福熹、李青会以及潜伟等学者都对该批玻璃珠进行过分析研究。其中,干福熹等对这批玻璃进行了成分分析,将其划分为两大体系:钠钙玻璃(Na2O-CaO-SiO2)和钠钙铅玻璃(Na2O-CaO-PbO-SiO2),并且初步认为这批玻璃珠借鉴了中西亚地区的玻璃制造技术,采用当地原料制备。李青会等利用多种成分分析技术对这批玻璃进行分析,将其大致分为三大体系:钠钙玻璃(Na2O-CaO-SiO2)、钠钙铅玻璃(Na2O-CaO-PbO-SiO2)和钙镁(铅)玻璃(CaO-MgO(PbO)-SiO2,其结论认为这批玻璃有可能由西亚等地传入,也可能传入技术后在当地自制。潜伟等对这批玻璃珠进行扫描电镜观察与微区成分分析,认为钠钙玻璃的生产与当地的炼铜活动之间存在联系,而含铅玻璃则与铅矿冶炼有关。这些认识的得出,主要是基于克孜尔水库墓地的部分早期玻璃中具有较高的PbO、Sb2O5含量,研究者将其视为西方玻璃技术本地化的证据。至2014年,李青会等对这批玻璃进行了化学成分、显微结构及物相结构方面的分析,将其分为植物灰型钠钙玻璃和钾玻璃两大体系,并从中识别出锑酸铅(Pb2Sb2O7)、锑酸钙(CaSb2O6)等晶体颗粒,明确了这批玻璃高铅、锑的原因,即玻璃中人为加入了锑酸铅(Pb2Sb2O7)和锑酸钙(CaSb2O6)作为乳浊剂,这类原料在埃及、西亚等地自青铜时代起就已被广泛用于玻璃生产。因而研究者最终认为该批钠钙玻璃珠与来自埃及和地中海东部的玻璃很相似,至于其是否是利用外来技术和原料在本地进行生产的则尚不能确定,那些器型简单、制作粗糙的蜻蜓眼玻璃珠可能利用外来原料在本地生产,而钾玻璃珠则有可能来自印度北部,对于其原始的生产情况目前还尚不明确。
除对拜城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玻璃珠的研究外,近十年来,李青会、刘松以及温睿等学者都对新疆地区早期铁器时代不同遗址出土的玻璃制品进行过分析研究,图一展示了这一时期新疆各地出土玻璃的分类及各类型占比。从图中可知,新疆地区早期铁器时代发现的玻璃基本上集中在天山廊道沿线,器型均为小件珠饰,成分上可以分为钠钙玻璃(Na2O-CaO-SiO2)、钾玻璃(K2O-SiO2)和铅钡玻璃(PbO-BaO-SiO2)三类。其中,钠钙玻璃多以高钾高镁的植物灰型钠钙玻璃(v-Na2O-CaO-SiO2)为主,而在吐鲁番洋海墓地和哈密五堡墓地则发现了疑似低钾低镁的泡碱型钠钙玻璃(m-Na2O-CaO-SiO2)。此外,钾玻璃在新疆这一时期的几处遗址也有所发现,从成分上看,该批玻璃均属于中等钙铝型钾玻璃(m-K2O-CaO-Al2O3-SiO2),研究者普遍认为该类玻璃很可能从印度地区传入新疆。从目前的分析数据看,该类玻璃有使用Mn3+着色剂和SnO2乳浊剂的情况,该类着色剂和乳浊剂少见于用于这一时期其他类型的玻璃,因此,对该类玻璃着色剂和乳浊剂的深入研究,可能能为进一步确定该类玻璃的来源提供重要的信息。另外,这一时期铅钡玻璃(PbO-BaO-SiO2)在新疆地区的发现,则反映了该时期中原地区对于新疆地区的重要影响。总之,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之后,随着游牧化进程在新疆地区的全面普及,新疆地区开始出现成熟的玻璃珠饰,并且种类和数量逐渐丰富,指示着这一时期该地区东西方文化交流更为复杂和多样化的面貌特征。
除对助熔剂成分的分析,这一时期新疆地区发现的玻璃还存在使用锑基着色剂/乳浊剂(Pb2Sb2O7,CaSb2O6)、锡基乳浊剂(SnO2)和钴蓝颜料(Co2+)等着色剂和乳浊剂的情况,对这些特殊着色剂和乳浊剂的来源展开深入探究,将会为解决这些玻璃制品的产地问题提供更多的线索。
汉晋时期,新疆地区出土玻璃制品的数量和种类都较前一时期显著增加,使用的工艺技法更趋复杂。天山南麓的尉犁县营盘墓地、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民丰尼雅遗址、且末扎滚鲁克墓群以及洛浦山普拉墓地等遗址都出土了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玻璃制品,其中以玻璃珠饰为主,亦有玻璃器物发现。这一时期各遗址出土玻璃的分类及各类型占比见图二。
从图二可以看出,与早期铁器时代相比,新疆汉晋时期发现的玻璃制品不仅出现在天山地区,在塔里木盆地南缘亦有诸多发现。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一时期天山以北各遗址出土玻璃制品的数量和种类远少于天山以南的遗址,而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线出土玻璃制品的成分类型则呈现不同的特征。具体而言,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以北各遗址出土钠钙玻璃以植物灰型钠钙玻璃为主,且根据K2O含量(>4wt%)大部分归入中亚类型组,少部分K2O含量较低的玻璃归入西亚类型组。而在塔里木盆地以南的丝绸之路南道上,则有多个遗址都发现了典型的泡碱型钠钙玻璃,相关研究者均认为这类玻璃源自罗马帝国。此外,位于丝路南道的这些遗址也均发现了较多的植物灰型钠钙玻璃,可根据其K2O和Al2O3含量分为西亚产地(低钾低铝)、中亚产地(高钾)和南亚产地(高铝)三种类型。从目前的研究看,丝路南道发现的植物灰型钠钙玻璃以南亚类型居多。有趣的是,塔里木盆地以北的丝路北道各遗址则广泛分布着中等钙铝型钾玻璃,研究者均认为这类玻璃最大可能源自印度,而这类玻璃在南道却仅有零星发现。因此,高铝型植物灰钠钙玻璃和中等钙铝型钾玻璃产地虽均源自南亚,但二者在新疆地区的分布范围却迥然不同,这似乎暗示着这两类玻璃很可能来自南亚不同产地,由不同人群经不同路线带入新疆地区。此外,这一时期铅钡玻璃主要发现在天山以北区域,天山南麓及丝路南道沿线则仅有零星发现,这一现象可能与同时期我国铅钡玻璃总量逐渐减少,并向下一阶段的铅玻璃及钾铅玻璃类型过渡有关。
与早期铁器时代相比,新疆地区汉晋时期出土的玻璃制品不再限于单色珠或造型简单的蜻蜓眼珠饰,其类型更为丰富多样,出现了绞胎玻璃珠、马赛克玻璃珠以及磨花玻璃器等多种具有强烈产地指征的特殊器型,图三展示了这些特殊器型的玻璃制品以及它们各自产地出土的相似玻璃制品的照片。例如,成倩等结合成分数据和纹饰特征,判断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的一枚绞胎玻璃珠产自古印度(今巴基斯坦)的Bara遗址,林怡娴在尼雅遗址发现了类似的绞胎玻璃珠,同样将其产地归入Bara遗址。刘念等通过对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的一枚人面纹玻璃珠进行成分分析和表面形貌观察,认为其可能使用了源自中亚的植物灰型钠钙玻璃,在泰国南部二次加工制成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后传入新疆。成倩等通过对且末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一件磨花玻璃杯进行成分和工艺研究,认为其可能源自今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巴勒斯坦海湾;安家瑶对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的类似的磨花玻璃杯进行分析后,亦认为其可能源自罗马帝国统治区域;而林怡娴则通过系统对比同时期世界范围内发现的磨面纹玻璃器的器型、纹饰和工艺特征,认为新疆地区出土的这两件磨花玻璃杯的具体产地可能在欧洲的黑海北岸。
随着汉晋时期新疆地区多种类型玻璃制品被大量发现,这些发现为深入认识汉晋时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证据,同时也拓宽了丝路研究的视野。
目前,对新疆地区南北朝至宋元时期出土玻璃制品的科技考古研究不多,且分析样品多为遗址采集品,部分玻璃所属遗址年代范围跨度较大,具体年代信息不详。对于这部分玻璃制品的研究,主要见于史美光等和李青会等对喀什、和田、库车以及伊犁等地遗址采集的玻璃进行综合分析,这一时期的玻璃除包含玻璃珠、管和环等小件器物外,也包括玻璃杯、瓶等大件器物的残片,特别是发现了大量利用吹制法制作的玻璃器皿。分析结果指出,这一时期该地区出土的玻璃主要为钠钙玻璃,其中以植物灰型钠钙玻璃最为常见。刘松等通过K2O、Al2O3、MgO和CaO等元素含量对这一时期发现的钠钙玻璃制品的产地来源进行进一步区分,认为这批玻璃的产地可以分为萨珊/伊斯兰、中亚、南亚和希腊—罗马几处,亦有部分产品可能系新疆本地生产。最近,徐思雯等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约公元4~8世纪)出土的一批玻璃珠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该批玻璃珠属于植物灰型钠钙玻璃,应属萨珊王朝产品,采用印度—太平洋珠所用的拉制法工艺制成,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萨珊玻璃工匠已经掌握了制作印太珠的技术,其生产的玻璃珠饰经由陆路丝绸之路传入新疆。此外,温睿等对新疆宋元时期也木勒遗址出土玻璃进行了工艺与成分研究,认为该遗址出土玻璃属钠钙玻璃,采用了以草木灰为原料的混合碱助熔剂,从成分特征看可能与同时期中亚生产的玻璃制品同源。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新疆地区的玻璃制品基本属于普通实用性器皿,已经广泛进入了平民的日常生活中。
整体来看,新疆地区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玻璃制品主要为钠钙玻璃,其中以来自萨珊王朝的植物灰型钠钙玻璃为主,兼有少量中亚类型植物灰钠钙玻璃、罗马帝国的泡碱玻璃、来自南亚、东南亚一带的矿物碱钠铝玻璃以及来自中原地区的铅玻璃,说明这一时期新疆地区的玻璃制品仍然以域外输入为主,存在远距离的贸易交流。至宋元时期,新疆出土的玻璃制品则以中亚来源为主,兼有新疆本地制作的产品,玻璃制品的长距离输入基本不复存在。
新疆地区自青铜时代起就开始出现费昂斯制品,至公元前1000年开始出现玻璃制品,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玻璃质实物材料年代最早的地区。自战国时期开始,新疆地区的玻璃制品呈现出类型多样、来源复杂的特点,这一特点至两汉魏晋时期更为突显。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新疆地区出土玻璃制品的来源涵盖我国中原、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以及欧洲等多个地域,几乎包含了钠钙玻璃、钾玻璃、铅钡玻璃以及混合碱玻璃四大类玻璃的主要生产中心,是我国发现玻璃类型最为丰富的地区。可以说,以四大玻璃技术为代表的“玻璃文化圈”在新疆地区实现了交汇,反映了各个时期来自不同区域的玻璃制品和技术在新疆地区碰撞交流的盛况。
与丰富的出土实物材料相比,新疆地区不同时期玻璃制品的系统化研究还相对薄弱。通过对新疆古代玻璃科技考古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时代上多集中于战国到汉晋时期,而对年代较早的费昂斯制品和汉晋之后的玻璃制品的研究则明显偏少。即使是研究者涉及较多的战国至汉晋时期,经分析测试的样品数量与玻璃制品实际出土量相比也远远不够,当前的研究成果还难以反映一个时期内新疆地区不同类型玻璃制品的基本组成和分布特征。特别是汉晋时期的部分研究偏好于对一个遗址出土的某件或某类形制特殊的玻璃制品进行分析,进而确定单件或几件同类型器物的产地,而缺乏结合遗址背景的玻璃成分大数据分析。而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玻璃制品的研究几乎都为单个遗址点的个案研究,缺乏多个遗址点间的对比研究。此外,在分析方法上,目前新疆地区玻璃制品研究多采用通过主量元素确定玻璃制品的助熔剂类型,根据不同玻璃的成分体系判断其大致来源,缺少国际上常用的微量元素分析和同位素分析来进一步细化不同玻璃制品的产地。因此,对新疆地区不同时期出土玻璃制品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进一步厘清不同类型玻璃制品的分布情况、构建该区域玻璃技术发展演变的时空框架仍然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此外,深入结合玻璃制品出土的考古背景,以获取这些材料更为精确的年代信息是未来研究推进的重要基础。而微量元素分析、同位素分析等技术手段的引入与应用、相关数据库的建立和完善,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只有将考古遗址背景、古玻璃的类型学研究、科技分析数据三者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推进并逐步完善新疆地区古代玻璃的研究。